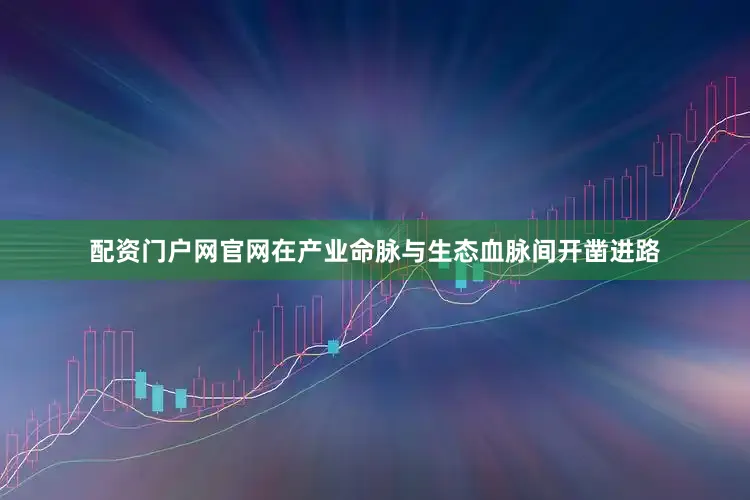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最初发表于1927年3月广州《国民新闻》副刊《新时代》,后收录在鲁迅的《集外集拾遗》中。1927年2月中旬,鲁迅应邀在香港作了两次讲演:18日的讲题为《无声的中国》,19日的讲题为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。这是一篇讨伐封建专制文化和旧意识形态的战斗檄文,是向旧传统观念发出的勇猛的挑战。
在这篇文章中,鲁迅直接批判说:“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,调子是最老的,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。”鲁迅撕开了专制文明华丽外衣下那令人窒息的本质——一种凝固于时间尘埃中的“侍奉文化”。他以其特有的冷峻笔锋指出,这种文化“是要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”,它内化于社会肌理深处,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。
老调子不绝,侍奉主子的千年循环展开剩余77%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这古老箴言并非虚言,它勾勒出权力金字塔的森严图景。君权如天穹般笼罩四野,将天下财富、土地、生灵尽收囊中。在此之下,众生皆为“臣”,皆需“侍奉”。权力成为唯一值得追逐的太阳,照耀着整个社会架构。历代王朝虽更迭不休,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到明清的中央集权,其本质始终如一:权力高度垄断,从无制衡分权之念。此种权力如饥饿的巨兽,贪得无厌地吞噬一切资源与意志,所谓“安心”“放心”“安全”,不过是权力独占后病态的自洽逻辑。
权力金字塔的运作依赖于自上而下的“任命”链条。官吏的权柄非自土地生长,也非人民赋予,全然源于上级乃至君主的恩赐。于是官场规则清晰而残酷:官吏的忠诚与仕途只对授予其权柄的上级负责,民众的福祉与声音被这冰冷的权力链条无情过滤、抛弃。民众被制度性地剥夺了监督、质疑与知情之权,只余下无条件服从的沉重义务,沦为赋税与徭役的无尽承担者。
此种制度生态下,“侍奉”成为生存的通行证。官吏们为保乌纱、谋晋升,无不精研“巴结”“讨好”之道。民众若想在这庞大机器下觅得一丝喘息空间,也只能以“顺从”“温顺”换取微弱的安全。鲁迅曾尖锐揭露其中的虚伪与奴性:“倘不是笨牛,读一点就可以知道,怎样敷衍、偷生、献媚、弄权、自私,然而能够假借大义,窃取美名。”稍有异议或反抗者,必遭国家暴力机器的无情碾轧。于是,整个社会弥漫着对权力的歌颂,对“主子”的侍奉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文化姿态——这便是鲁迅所痛斥的“侍奉文化”的根源。专制孕育奴役,奴役锻造奴隶,奴隶则以其深入骨髓的奴性为专制提供最稳固的基石。
沉重的文化积淀与奴性交织,如同鲁迅所言的“割头不觉死”的软刀子,使社会“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,害得一切硬化”。国粹被奉若神明,执念深入骨髓,社会机体在时间洪流中日益僵化,丧失了新陈代谢的活力。国民性由此被惰性主导:保守、愚昧、安于现状、不思进取。正如鲁迅辛辣描绘的:“只要从来如此,便是宝贝。他们对于旧状况总是心平气和,对于新机运往往疾首蹙额,对于已成之局老是委曲求全,对于初兴之事则常常求全责备。”
这种文化惰性与旧制度的合力,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。任何试图突破的新思想、新学说,要么被这强大的“酱缸”无声消融,面目全非;要么在激烈冲突后铩羽而归。若无彻底决裂的勇气与更激烈的革新方案,仅寄望于温和改良,则旧制度强大的回旋之力必将一切拉回原轨,使变革归于“一事无成”。每一次看似翻天覆地的王朝更迭,不过是“主子”姓氏的轮换,权力垄断的本质结构岿然不动,社会运行规则依然如故,唱响的仍是那千年不变的老调子。
鲁迅在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中的呐喊,那“老调子”真的唱完了吗?当“侍奉”的幽灵仍在某些角落徘徊,当权力任性的魅影尚存,答案不言而喻。老调子从未真正唱完,它只是间歇性地沉默,伺机在历史的某个转角再次响起,如同一个无法摆脱的沉重诅咒。走出这循环,需要的不止是觉悟,更是对文化中深植的“主奴”结构的彻底清创与再造。老调子未绝,新声何在?这问题悬于历史的空谷,等待着一代又一代不愿做侍奉者的灵魂以行动作答。
发布于:江苏省配资门户平台,股票配资资讯平台,十大配资排行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